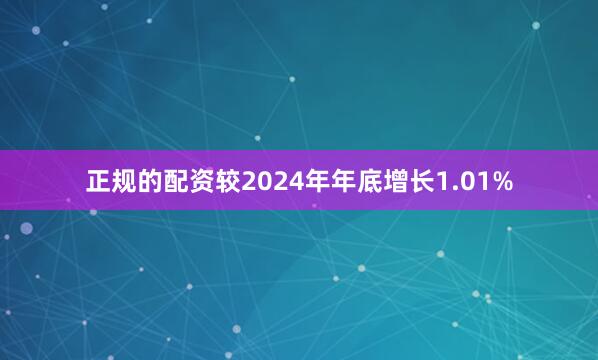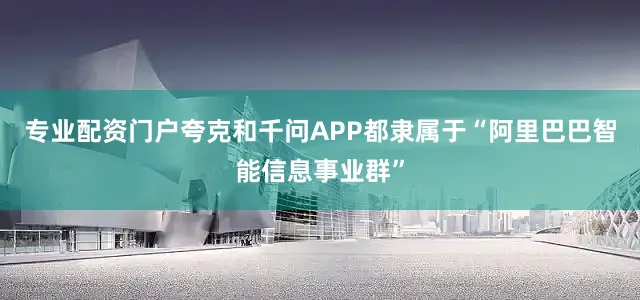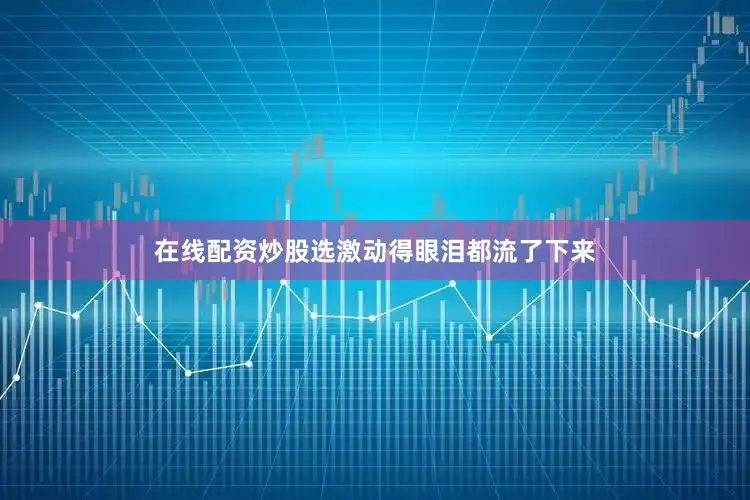
清朝年间,有位在江上讨生活的贫苦船工,某日外出如厕时,脚下意外踩到的并非致命地雷,而是命运的奇妙转折。
谁能料到,这一蹲,竟蹲出个不凡人物。
江上苦命船工
江苏高邮,江水滔滔,寒风四季肆虐不停。此地水道纵横,码头林立,可谋生的法子却少得可怜。
张拙,就生长在这样一个逼仄困苦之地,最终无奈成为船上的一员。
家中一贫如洗,连口像样的锅都没有,母亲卧病在床,父亲早早离世,几个兄弟姐妹全靠他一根扁担在江里讨生活。
十六岁那年,他登上了船。寒冬腊月,双脚赤裸;炎炎夏日,烈日暴晒。一年到头,手上老茧厚得能用来擦锅。
展开剩余90%船上的活计繁重无比,每日扛包、摇橹、烧饭、扫舱,全得靠自己硬撑。人们常说,水上漂泊有两种结局,一种漂到安稳的岸,一种漂进冰冷的棺材。
张拙年纪尚轻,苦累倒也不怕,只是觉得人生毫无盼头。有一回,在扬州码头深夜卸货,绳索突然断裂,几十斤重的木桶砸下,他的头被砸破,鲜血直流。他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,游上岸后又接着干活。
伤口缝了三针,却没钱买药,只能随便捡些草药敷上。
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张拙有三百天都睡在狭窄的仓板底下。
在船上吃饭,得看船主的脸色。运气好时,能管顿饭;运气差时,就得自己想办法填饱肚子。
最难熬的,不是饿肚子,而是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命如草芥,活得就像船底的水草,无人问津。
初夏奇遇
那年初夏,天气闷热得如同蒸笼,江面都弥漫着热气。船停靠在镇江口,船主接了一单盐货,暂时停航。张拙闲来无事,又没法下岸,只能窝在船舱里打盹。
两天前,他吃坏了肚子,一直疼痛难忍。这天一早,实在忍不住了,他翻过船帮,跳到岸边的树林里,想找个地方解决内急。
这一步,看似走错,实则踏入了命运的奇妙棋局。
意外之财的抉择
张拙猫着腰走进树林,刚蹲下没多久,忽然感觉脚边一阵松动。他以为是树根,不经意间一瞥,竟发现一个半埋在土里的包袱角露在外面。
灰色的麻布包袱,边角已经破损,露出里面一角黄澄澄的金属。
此时,太阳恰好从树缝间洒下,那点光芒刺进他的眼睛,如同锋利的刀子般明亮。
他整个人瞬间愣住,那光芒绝非铜色,而是银子和金子交织反射出的璀璨之光,就像船老板腰间挂着的金扣子,只不过眼前这可不是区区一块。
张拙双手颤抖着扒开包袱,麻布一扯,里面两根金条、一大把碎银,还有几个包得严严实实的丝绸小袋映入眼帘。
他一下子瘫坐在地上,脑门上冒出了冷汗。
他的脑海里瞬间闪过三个念头:这是谁的财物?要不要据为己有?拿了之后能不能顺利脱身?
这片林子位于镇江渡口边的小杂林,来来往往的船只众多,谁扔的、谁埋的,早已没了踪影。
张拙心里七上八下,他扯着包袱站起来,望了望不远处船的方向,双腿却像灌了铅一样,无法挪动。
那一刻,他心想,要是拿着这些金银跑了,这一辈子所吃的苦,都能换成金银财宝,换成热气腾腾的饭菜,换成崭新的船只,换成美好的日子。
然而,他最终还是克制住了自己,将包袱原封不动地埋好,拍了拍土,坐在旁边的树下等待。
等谁,他心里也没底。
大约过了一炷香的工夫,林子那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一个中年人慌慌张张地跑过来,嘴里不停地喊着什么,看样子焦急万分,快要发疯了。
张拙没有说话,只是指了指脚边。
那人一下子跪在地上,疯狂地挖出包袱,一看东西都在,激动得眼泪都流了下来。
他什么也没说,从怀里掏出一块碎银就往张拙手里塞。张拙没有接,只是站起来淡淡地说了一句:“还给你。”
那人离开后,张拙回到了船上。当天下午,船上一个富绅家雇来探路的伙计来找他,说员外要请那位拾金不昧的船工过去吃顿饭。
张拙想了想,收拾了个包袱就跟着去了。
命运转折之门
张拙跟着管家走出林子,踏入了镇江城。街上人来人往,热闹非凡,可他却感觉像是踩在棉花上,心里空落落的,后背早已被汗水湿透。
那一包金银,他连多摸一下的勇气都没有,埋回土里后,坐在那里等失主,脚底下发麻,心里也七上八下。
他不知道那一刻自己该何去何从,往回走是熟悉的老路,往前走却无人引领。
李家宅子位于镇江南门外,朱红色的大门威严庄重,门匾上“仁义”两个字被擦得锃亮。
那天刚下过雨,门前的石阶还湿漉漉的。管家恭敬地请他进门,奉上香茶,却对金银之事只字不提。
坐了小半个时辰,李员外才缓缓走进来,脸上带着疲惫之色,眼神却沉稳有力。茶还没凉,他便开口说道:
“你那双眼睛没看错,确实是金子,可你没拿,这说明你身上还有更宝贵的东西。”
这话让张拙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。他在船上扛了多年麻袋,靠力气吃饭,从未有人正眼瞧过他,今日被人如此看重,倒让他浑身不自在。
员外没有多说,把管家叫来,让张拙留下做事。
起初,张拙在外院帮工,送货打杂、洗车挑水,虽然辛苦,但一日三餐倒是能吃饱。
李家下人众多,能进内院的没几个。张拙深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,于是天天第一个起床,最后一个睡觉,干活积极主动,绝不允许自己出一点差错。
夏天运煤,别人嫌脏,他却毫不犹豫地扛起;冬天送盐,别人怕冷,他总是第一个出发。三个月下来,管家主动让他进了内账房,负责递纸送笔,帮账房先生抄账。
他不识几个字,夜里便借了李家仆人的破书,一边对照着账本,一边死记硬背。
三个月的时间,他抄坏了三支毛笔,笔头磨得几乎不剩一寸。
慢慢地,人们都知道后院有个“抄账的船工”,字写得工整,脑子也灵活。
账房让他单独抄货单,试着算账头。有一次,老账房算错三文钱,张拙指出来时,满屋人先是一愣,随后发出一阵冷笑。
账房先生却不恼怒,重新拨动算盘一算,果然少了三文。
从此,没人再敢小瞧他。那晚饭后,员外特地让人送来一只银饭盒,菜比别人的多两样。
三年后,李家分号增加了两家,张拙成了副账,外头人见面都尊称他为张账爷。
往来商客落座时,常常问起他,李员外总是笑着说:“他是个拾银子的命好人。”
临危救难显担当
那年秋天,李家有三船木材要运往扬州。张拙受命押货同行。
途中,江面突然起风,行船变得摇摇晃晃,十分不稳,后两船很快失去了联系。
张拙仔细查看过天气,见风向逆急,果断判断应该靠岸改道。
他命令前船就地卸货,换小船分批运送。结果刚靠岸不久,风浪便猛烈起来,后两船翻覆,十余人落水,仅三人游上岸。若再晚一刻,他恐怕也难逃一劫。
回到镇江那天,李员外迎到门口,没有摆宴,也没有送礼,只是一起吃了一顿家常饭。
他端起碗,感慨地说:“张账爷救的不是货,是命啊。”
张拙低头扒饭,没有应声,手里的碗却稳如磐石。
接下来,账房全权交由他执管。
李员外年老体衰,将内外总账交给他,只嘱咐他一个原则:别动歪心思,账目要清楚,人才能安稳,银子才能长久。
张拙默默记在心里,眼神更加坚定,算盘拨得更快了。
外人都说张账爷清廉得像铁砧,连李少爷也不敢赊账。
五年过去,李员外抱病在床,家中大小事务皆由张拙打理。
晚秋某夜,员外命人叫他入房。屋内香炉尚暖,帘外风吹松枝沙沙作响。老员外只说了一句:“你早晚要开自己的商号。等我闭眼,就从‘拙记’起步。”
张拙顿首三拜,一言不发。
员外去世当日,全镇江的商号皆来吊唁,送挽联的有盐商、有茶行、有船队老东家。
张拙身穿粗布长衫,跪在灵前,礼数一丝不差。满城人都说他得了李家半壁江山,可他的神情却依旧如初。
江上之人,岸上新命
丧事过后三个月,“拙记”的招牌挂在了镇江南门外。
铺面不大,一进一出两间门,窗前挂着一对灯笼,上面写着“通货达财,记德守信”。
开张那天,张拙亲自站在柜台前,不吆喝、不张扬,只是静静地坐着,等待客人上门。
第一日过午,来了个穿短褂的客人,是原先李家账上的老主顾。他见张拙依旧亲迎亲送,账单清清楚楚,当即签下三千两订货。
往后三个月,老主顾陆续来访,“拙记”的生意越做越大。张拙却没有搬进大宅,仍住在原李家旧院,起早抄账,午后查货,亲自收银,不交给旁人。
一年内,他设立了三处分号,扬州、淮安、苏州皆有掌柜坐镇,全是他亲手挑选。
每月调账一次,每笔账他都亲自过目。手下人都知道拙记规矩严过朝堂,一分误差必追三层查账。
老船上的人闻讯而来,十人之中有七人愿意投奔他。
张拙没忘当年在水上的苦日子,他设立了水手病养银、丧葬银、妻小抚养银,每年冬月放银买棉衣,人人都称他“拙东家”。
他亲自去码头送棉衣,说自己当年也是冻出来的命。
镇江水患那年,他带头修堤,捐银五百两,买砖万块。地方官赐匾一方“济世同舟”,高高悬挂在拙记门前。
那夜,有人问他为何如此。
他只回:“当年我蹲在林子里拉肚子,差点饿死,抬头见天,地下埋着金银。我没拿,天就没拿我命。”
从前船上的一个杂工,走到商号掌柜的位置,靠的不是偶然的机会,而是守住了心里的一条底线。
金银堆在脚下,他没动,李员外看在眼里;账本掀在手中,他没错,客户才放心跟他合作。
归隐田园
张拙六十岁那年,关门退隐,把拙记交给账房长子,自己去扬州买了块菜地种菜。
他说,够了,活得明白比活得富贵难得多。
他晚年写了一句字,贴在堂屋正中:“起心无邪念,行事有尺度,江湖天地宽。”
发布于:山东省广盛网配资-免费配资炒股配资平台-配资平台官网-如何选择股票技巧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